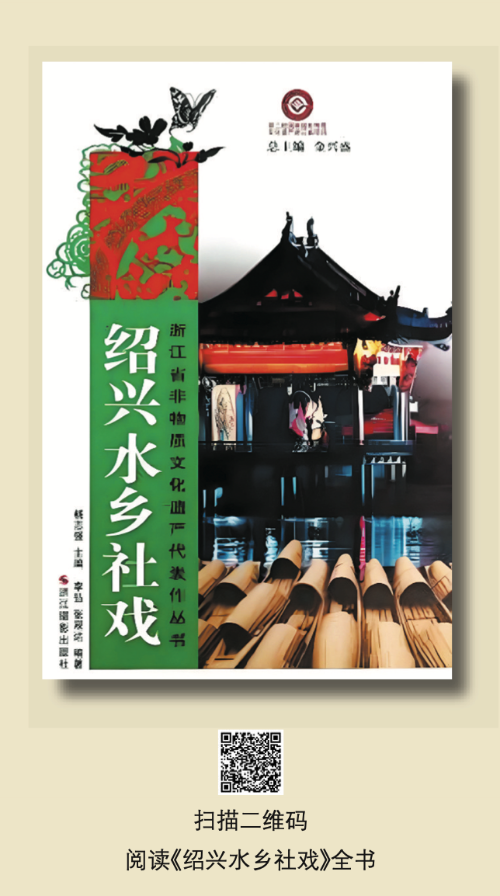|
乌篷船上看好戏 |
|||
|
|||
|
俞盈盈 撑一只航船,船篙一磕桥石,几个孩子就迎着夜风和流水,穿向乌篷船涌动水域——“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,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,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,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,就在这里出现了。”百余年前,鲁迅这样描写一个少年在家乡看戏的经历。水乡社戏的幻妙而真切、农家好友的诚挚与机灵,成为此后代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。2008年,绍兴水乡社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乌篷船上看社戏 ●社戏遇水乡 “社戏”二字,一来缘起于“社”,是独立的祭祀单位;二来表现为“戏”,融贯歌舞与文学,并逐渐汲取民间活动的烟火气,从严肃的宗教仪式发展为热闹诙谐的世俗表演。 绍兴自古河网密织,“出门就是水,抬脚得用船”,素有“万桥之乡”的美称。正是这一环境特点,孕育出了水乡社戏这种独特的文化遗产。它的起源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祭祀活动,那时常有人喜在河台前歌舞唱跳,尤其在农忙结束之后便大兴活动。慢慢地,与戏曲紧密结合,形成了“社—祭—戏”相统一、相融合。 到南宋时期,社戏便已十分盛行。陆游的诗《春社》中就有过描写:“太平处处是优场,社日儿童喜欲狂。”对于当时百姓看社戏的热闹场面,他还曾写道:“空巷看竞渡,倒社观戏场。” 元明时期,民间社戏迎来了兴旺鼎盛的局面。春祈秋报、节日盛典、迎神赛会等时日,戏场锣鼓喧天、观众云聚。明张岱《陶庵梦忆》曾这样记录绍兴的庙会戏:“城中及村落人,水逐陆奔,随路兜截,转折看之,谓之‘看灯头’。五夜,夜在庙演剧,梨园必倩越中上三班,或雇自武林者,缠头日数万钱。唱《伯喈》《荆钗》,一老者坐台下,对院本,一字脱落,群起噪之,又开场重做……科诨曲白,妙人筋髓,又复叫绝。遂解维归。戏场气夺,锣不得响,灯不得亮。” 社戏四方皆有之,为何偏在越地最是热闹?鲁迅在《社戏》中以主角少年回忆的遥远好戏,唯此一处。未必在锣鼓之金贵或戏台之考究,而在农闲时分,船橹一荡,少长咸集,水波灯影,方言念白唱悠悠,乡邻看戏享自在。水乡社戏,是根植于人民生活的好戏。 ●唱神亦唱鬼 由于社、祭、戏合一,依照民间祭祀活动的由头,水乡社戏大致可分为年规戏、庙会戏、平安戏和偿愿戏。 顾名思义,年规戏是据年岁时令演出的社戏,包括不同季节祈求风调雨顺的时令戏,以固定节日搭台的应节戏(其中以元宵节最为热烈,中元节最为闹猛),还有各村自行安排的例行戏。庙会戏则是应庙会活动而行,以娱神谢神之由,集会祝福,神人共享。偿愿戏则意在祈愿谢神,除却旱季祈雨,求子、治病、盼归也在常见行列。 较为特殊的是平安戏,旨在祀鬼禳灾。平安戏主要分为目连戏和大戏,前者为业余戏班,每年约定挨村演出,俗语有“看一夜目连看一夜鬼”;后者则为专业戏班,若地方发生瘟疫或有人死于“五殇”(水、火、刀、自缢、分娩),特请戏班以祈解祓。 鲁迅对于平安戏亦有专门讲述,写有《女吊》一文。在故乡的社戏中,鬼魂并非完全恐怖陌生的非人之物,而是具有真切人情和风俗世相的动人角色,乃至于鲁迅借其发出赞美,这种以具有反抗精神的人民为原型的鬼魂角色是“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,更强的鬼魂”。 虽有死亡的无常与无奈,社戏对鬼魂的再现并未表现为一种屈从,而是以诙谐之态将其消解,并在唱与舞的夸张演绎之中,注入强健的生命之力。无论是在瑰丽庙台,还是在岸河戏台,“粗、土、俗、野”的社戏,总是反映了璞玉般的世俗活力与生命意志——“粗”在条框灵活,“土”在取材地方,“俗”在直面现实,“野”在敢于批判。 ●好戏复开唱 在新一轮对非遗项目的挖掘保护行动中,绍兴对戏台原址的保留和修复,使得“摇橹听戏”的文化场景得以留传;大型实景影画剧《鲁镇社戏》的沉浸式社戏体验,也使水乡风光与文化风尚深度融合;水乡社戏节、乌篷船比赛、社戏会市等,广邀老少乡亲共享文化佳肴,品味时代馨香。 如今,好戏又“开台”,邀君乘船来—— 锣鼓声声狂引客,丝竹悠扬请入座,这是热场的彩头戏,“请寿”“跳加官”“跳魁星”等轮番祝福观众延年益寿、升官发财、登科及第、福运共享、招财进宝。 紧接着,便是突头戏,即长篇大戏选段的折子戏,以“三折”为限,亮相唱、念、做、打的硬功夫,展现戏班本领,为台柱、头牌的登场做精彩铺垫。到了正本戏,名角压台,赢得阵阵喝彩。绍兴水乡社戏的八十多出剧目博采众长,《梁祝》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《白蛇传》《碧玉簪》《孟丽君》《宝莲灯》等兼有之。 至于收尾戏,或与“闹场”相呼应,或由老旦、净、末演员致意送客,或请“关公”“包公”上场“扫台”,让观众尽兴而归。 千百年来,绍兴水乡社戏招客来、送客去,从“活”的民间经验中生发,也在“活”的水乡风土中传承下去。鲁迅笔下社戏之夜的如梦似幻,正在一声声船桨激荡中,合奏为非遗传承的一场场锣鼓丝竹,一段段唱念做打。 |
|||